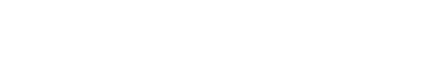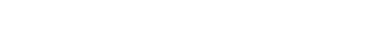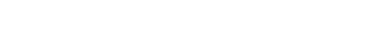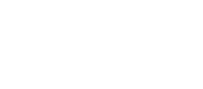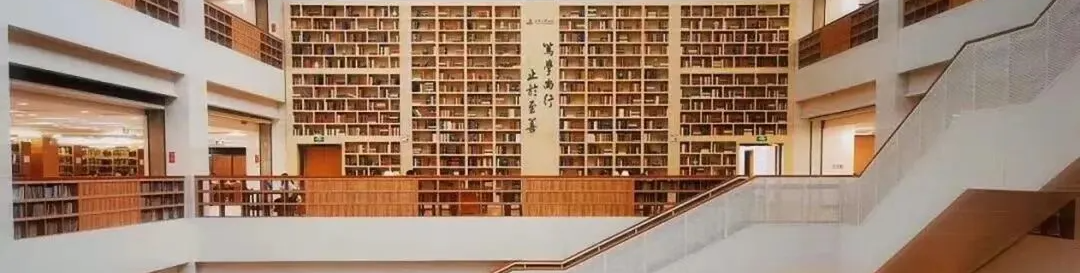一周一书 | 《被讨厌的勇气》:愿你有被讨厌的勇气,也有爱人的能力
在社交软件上反复编辑又删除的消息、聚会中不敢拒绝的无效社交、生活上违心附和的妥协……你是否也常被“怕被讨厌”的恐惧束缚?《被讨厌的勇气:“自我启发之父”阿德勒的哲学课》(岸见一郎,古贺史健著)在书中深入探讨了阿德勒心理学的思想。这本书像一把锋利的手术刀,剖开我们对人际关系的执念:真正的自由,始于不再寻求他人的认可。当我们学会把“别人怎么看我”的权重从生命天平上卸下,才能重新校准属于自己的人生坐标。

挣脱过去的枷锁:决定我们的不是“经历”,而是“赋予经历的意义”
“幸运的人一生都在被童年治愈,不幸的人一生都在治愈童年。”这句被广泛传播的话,道尽了弗洛伊德决定论的核心逻辑。但阿德勒作为弗洛伊德曾经的追随者,却掷地有声地提出反对: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,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。
书中的青年始终困在“家庭贫困”的阴影里,认为是童年的经济匮乏导致自己成年后不敢追求理想的职业。阿德勒却反问:“同样出身贫寒的人中,为何有人努力改变命运,有人却自甘堕落?”关键在于,我们如何解读过去。就像尼采所说:“杀不死我的,使我更强大”,但阿德勒进一步指出,“杀不死你的,是否让你强大,取决于你自己的选择”。

现实中,我们常常将失败归咎于原生家庭、成长环境,仿佛这些是无法改变的宿命。但阿德勒心理学如同刺破迷雾的利剑:过去无法改变,但未来可以重塑。就像日本作家村上春树,年轻时经营爵士乐酒吧,30岁才开始写作,他从未抱怨“非科班出身”的局限,而是专注于每天凌晨四点起床写作的自律。当我们不再做“过去的囚徒”,才能成为“未来的主人”。
课题分离的智慧:你的事与我的事,是两条平行的铁轨
在人际关系的迷宫中,我们常常因“过度介入他人课题”或“允许他人干涉自己课题”而痛苦。此书中探讨的阿德勒心理学提出“课题分离”,堪称破局的黄金法则:辨别什么是你的课题,什么是我的课题,尊重边界,是获得自由的前提。
大学生小林想选修一门小众的艺术课,但室友们都在选修热门的课程,认为这些课容易得高分,能积累实用的技能。小林在室友们的反复劝说下开始犹豫,甚至怀疑自己的选择是否正确,原本对自己选择的期待也被焦虑取代。按照课题分离的逻辑,“选艺术课”是小林的课题,“因小林是否选热门课而焦虑”是室友的课题。过度介入他人课题,涉足他人的人生抉择领域,本质上是对他人自由的侵犯;允许他人干涉自己课题,让渡自身的选择权,则是对自我价值的轻视。
生活中,我们也常陷入“同事评价”的漩涡。阿德勒提醒我们:别人如何评价你,是别人的课题;你如何对待自己,是自己的课题。就像画家梵高,生前不被认可,却依然坚持“画自己看到的星空”。当我们学会对他人的课题说“不”,才能对自己的人生说“是”。

共同体感觉的终极追求:在“他者贡献”中实现自我价值
既然课题分离强调边界,是否意味着人际关系的疏离?书中给出了温暖的答案:真正的自由,存在于与他人的联结中。这种联结不是控制与被控制的枷锁,而是基于“共同体感觉”的平等共生——把他人视为伙伴,在对他人的贡献中感受自己的价值。
“共同体”的范围可以无限扩大:从家庭到职场,从社会到宇宙。书中的哲人说:“当你在公园为陌生人捡起掉落的物品时,你就已经参与了宇宙共同体的建设。”这种贡献不是为了换取认可,而是源于“我对他人有用”的自我肯定。就像特蕾莎修女,她从未追求世俗的成功,却在为穷人服务的过程中找到了生命的意义。
现代社会的“空心病”,往往源于缺乏共同体归属感。我们沉迷于社交媒体的虚拟点赞,却失去了真实的联结。阿德勒心理学告诉我们:真正的价值感,不在他人的评价里,而在自己的行动中。当我们为父母做一顿饭,为同事分担一份工作,为陌生人撑一把伞,这些微小的贡献,都是点亮生命的星光。

阿德勒心理学像一面镜子,让我们看见自己如何用“讨好”编织牢笼,用“恐惧”锁住自由。但治愈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——正如书中青年与哲人的对话持续了整个夏天,我们的觉醒也需要时间的沉淀。
或许某天,你会坦然拒绝无效的社交,不再因“怕被讨厌”而委屈自己;或许某天,你会微笑面对他人的误解,因为深知“他人的课题无需负责”;或许某天,你会主动为陌生人递上援手,在“他者贡献”中听见内心的掌声。这不是自私的冷漠,而是历经课题分离后的通透,是懂得共同体联结后的温柔。
正如罗曼·罗兰所说:“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,那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”而此书作者阿德勒告诉我们:真正的勇气,是看清人际关系的真相后依然选择真诚——不怕被讨厌,也不害怕去爱。同学们,愿我们都能在这场关于“被讨厌”的修行中,遇见那个真实、自由、闪闪发光的自己。(编辑:易宇玲;审核:罗洪斌签发:赵玉宏)